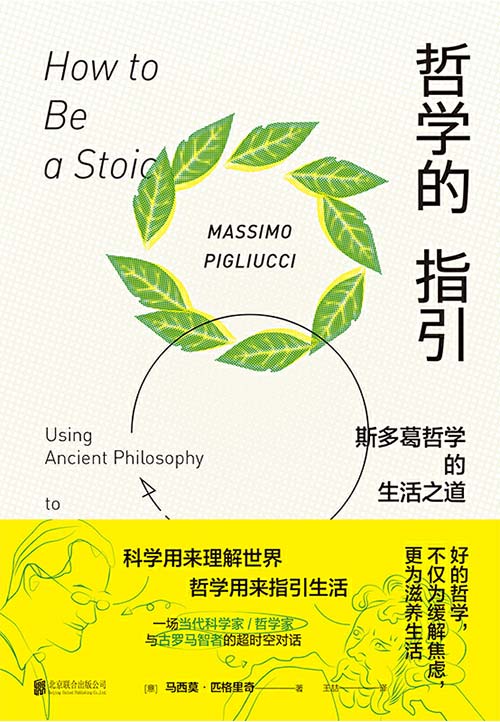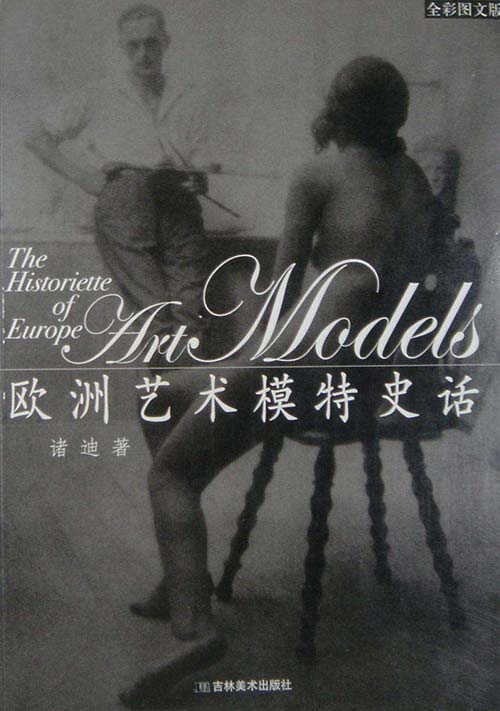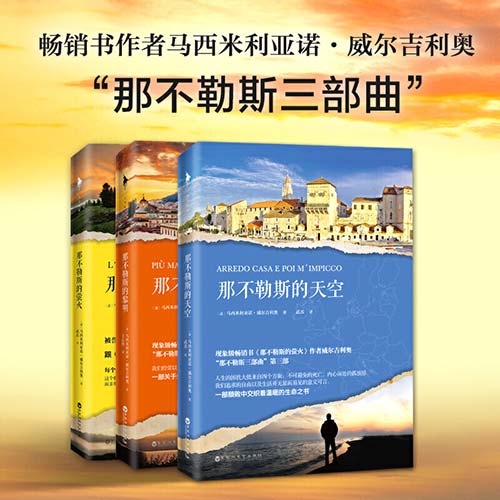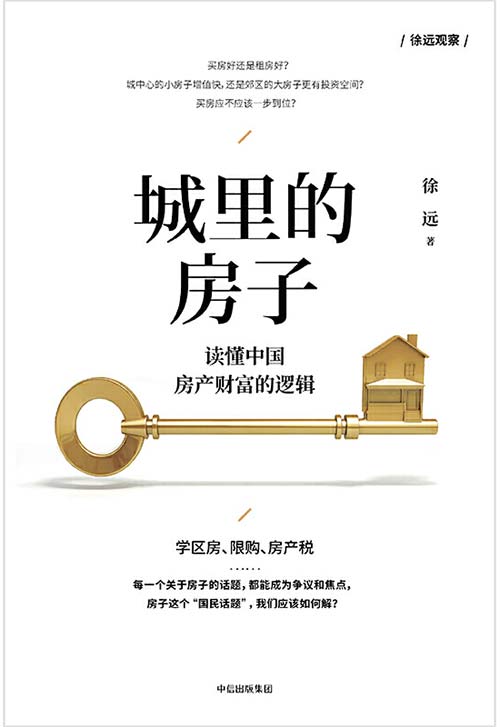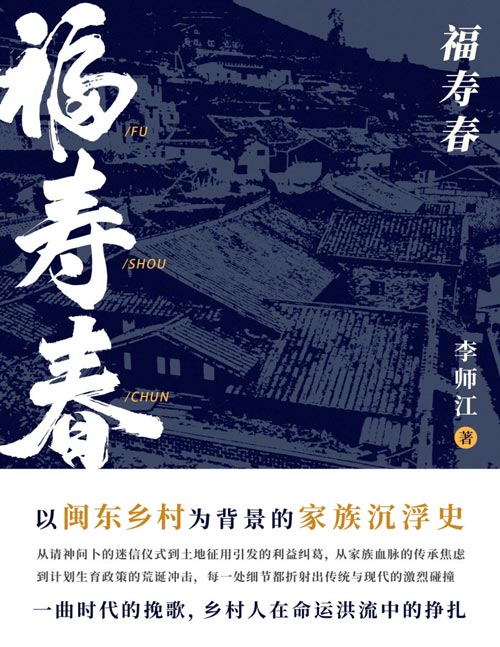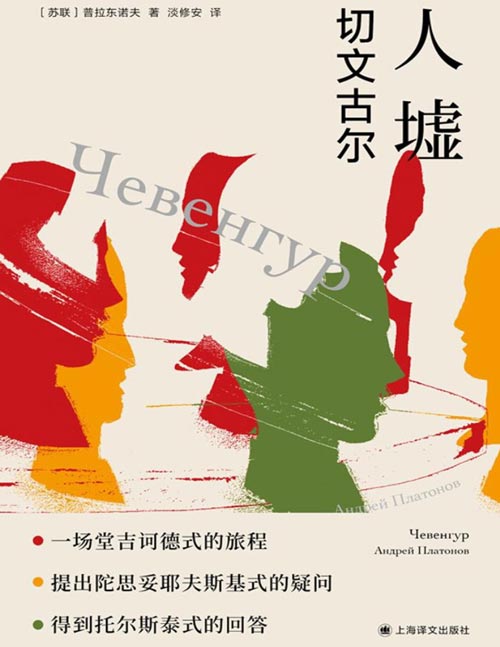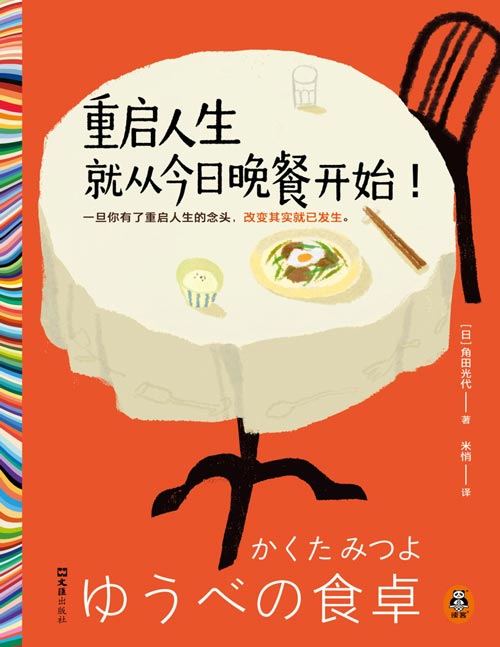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知名媒体人杨时旸首部长篇力作
这是一对普通“北漂青年”与“房子”不得不说的故事,主人公是你、是我——被房东驱逐,和中介周旋,跟房价赛跑……
我们不过是受够了不停地搬家,受够了房东充满审视的脸色,受够了居无定所;
我们不过是想活得安稳一点,能睡在自己的床上,再养一只猫……
这个现实生活的小小切片,记录着这个时代的荒诞与希望,身不由己和无法选择。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北漂买房”的小说。
刚毕业的杨天乐拎着旅行包,倒了两趟地铁,穿过一条曲折小巷和两个破败桥洞,来到了幸福里小区。?
像所有奔赴北京的年轻人一样,他相信这座城市是公平的。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那么在这里落脚扎根、生儿育女,一切都应该水到渠成。但他没有想到,连一个稳定的住处,在未来几年内都愈发遥不可及。
跟房价赛跑,与房东周旋,和中介博弈……他终于明白,在很多事情上,起跑线就差之千里。所谓的“公平”,只是一种程序正义,单靠几年的高等教育和不太笨的自己,跨越不了阶层。而如果这次买不到房,可能一辈子都买不到了……
这是一个现实生活的小小切片,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荒诞与希望
作者简介
杨时旸
80后。知名文化记者,多家媒体专栏作家,从事新闻行业十余年。现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著有杂文集《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人生》,影评集《孤独的影猎人》。
在线试读
搬家,无论经历多少次,也永远不会让人习惯和适应。这轻巧的两个字涵盖的其实是一种重大的生活变故: 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再栽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努力还魂。人的生活是由无比丰沛的细节组成的,搬家意味着把早已安之若素的所有细节粗暴地归纳。除非是游牧民族,不然没有谁愿意不停地迁徙。这个过程并不令人愉快。更糟糕的是,这一切还都是被逼迫的。
相较于找房子、收拾东西之类具体的劳累,被驱逐的感觉其实更令杨天乐难受,近乎屈辱。即便房东从未想过要高高在上,但他的角色让他具备了那种能力,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值一提。这种感受复杂、细腻又隐秘,杨天乐从未和钱潇提及。或许是觉得尴尬,或许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总之,每次搬家前,这种感受都会像牛胃里的食物一样自动反刍上来,杨天乐不得不一次次独自咀嚼,然后想办法努力咽下,等待再次被默默地消化掉。
其实他清楚,钱潇也应该有着同样的感受,只是在这件事情上,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沉默。有些事,在能够被真正解决之前,说出来也没有任何作用,只能平添烦恼。因为不知道如何沟通,说着说着就会变成撒气。和自己撒气,和对方撒气,然后不可避免地导向争吵,而且是无意义的争吵,再激烈也无法推动任何东西。最终,还是得平静下来。之后日子照常,两个人还得互相找台阶,从一种敌对、气愤、极端的情绪中逐渐回魂,那个瞬间,一切显得虚无又荒诞。也是在那个瞬间,杨天乐会最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能。于是后来,他竭尽全力避免让那种感觉滋长。他觉得自己未必经受得住太多次那样的侵蚀——有如冰水渐渐漫过全身。
对于搬家这件事的态度,杨天乐和钱潇其实经历过一条奇妙的弧线。最初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把搬家当回事,甚至觉得下班后一起收拾东西,在北京的夜晚拖着大包小包从一个住所搬去另一个住所,有种独特的乐趣。或者说,有一种象征意义,近乎外省青年必经的仪式,激发着他们的奋斗感和存在感。这种感觉在小城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决定来北京之初,他们早就知道将要面临的生活是怎样的。从学哥学姐那里听到过,从电视网络里看到过。蚁族、鼠族、城中村、握手楼……客观地讲,他们过得比那些传说里的故事好得多,并没有那么极端。但对于那一切,他们也是做过心理准备的,像绝大多数奔赴北上广深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自动对可能将要降临的苦难进行了美化。在某一个时间段内,颠沛流离和居无定所甚至会让他们萌生某种浪漫的诗意,但这诗意的产生和维系是有前提的,那便是:颠沛和漂泊只是暂时的,在不远的未来,他们可以得到稳定的生活,在闲暇的时光里,终能回望当年的苦难。换句话说,经历过的颠沛不过算是一种短暂的体验,会成为日后忆苦思甜的谈资。而一旦漂泊望不到尽头,那些柔和的光晕和浪漫的象征注定会消失殆尽。
有时候想想,生活就是个骨架,人们用希望对它进行了装点。希望破灭, 就只能看到森森白骨。到那个时候, 又有谁不会退缩呢?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长久陷入动荡和逼仄的生活不会产生什么正面的效果,相比于得到的磨炼,更多的其实是绝望。教科书上讲述的那些苦难的意义,在现实中像经不起任何查验的笑话。杨天乐大概在来到北京的第五年里洞悉了这一切。
那一年,经历第四次搬家的时候,钱潇崩溃过一次。当时,他们俩一起提着一个红白蓝三色交错的编织袋走上过街天桥,袋子质量很差,杨天乐走快了一步,钱潇没跟上,编织袋从拉链旁边撕开了一个口子,里面装着的两只锅、几个盘子还有一把筷子散落一地。盘子碎了,锅砸到地上发出钝重的响声,有几根筷子从天桥上掉下去, 砸在一辆过路汽车的车顶上, 然后迸溅开去。杨天乐走到天桥边,往下探身看了看, 说了句“真悬” , 然后就没当回事地回身开始收拾。他把盘子的碎片一点点踢到旁边,钱潇蹲下捡拾筷子,捡着捡着突然就哭了,毫无过渡和征兆。杨天乐在一旁手足无措。他愣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安慰钱潇,钱潇却扭向另一边哭得更加凄厉。杨天乐蹲在那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无力。
他本能地觉得这一切窘境都是自己造成的,是因为自己的无能,但又觉得好像也不全是如此。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念头冒出来,又突然觉得是在推卸责任。他不知道谁该对这一切负责,自己好像连揽下责任的能力都没有。一切开始混乱。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杨天乐觉得大脑里的一切都被冻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