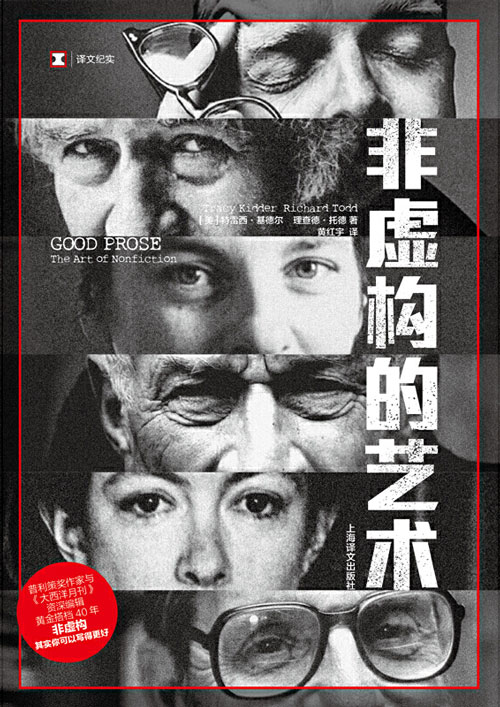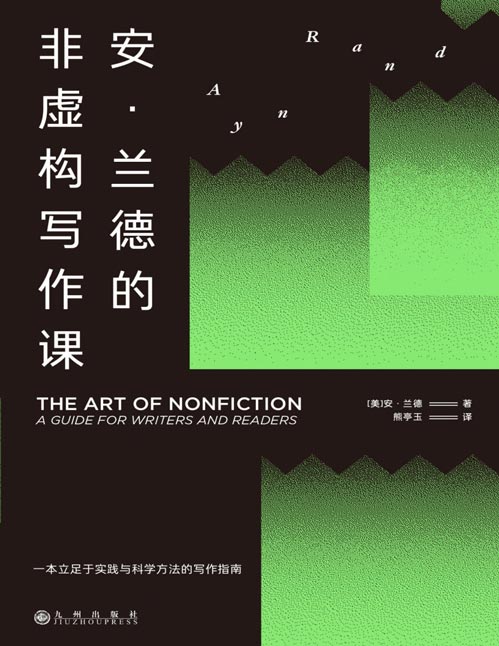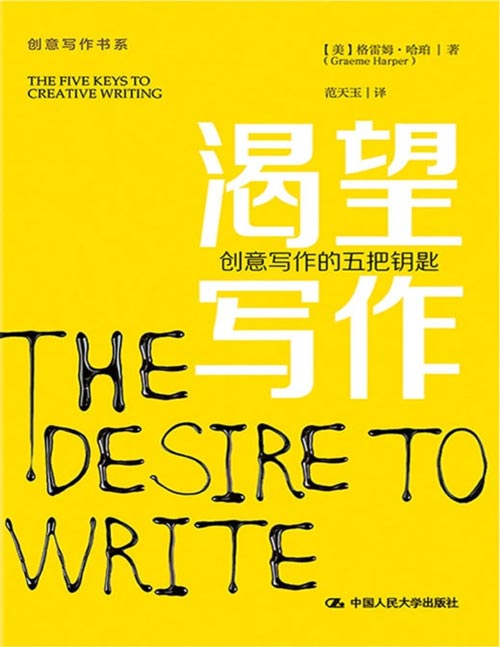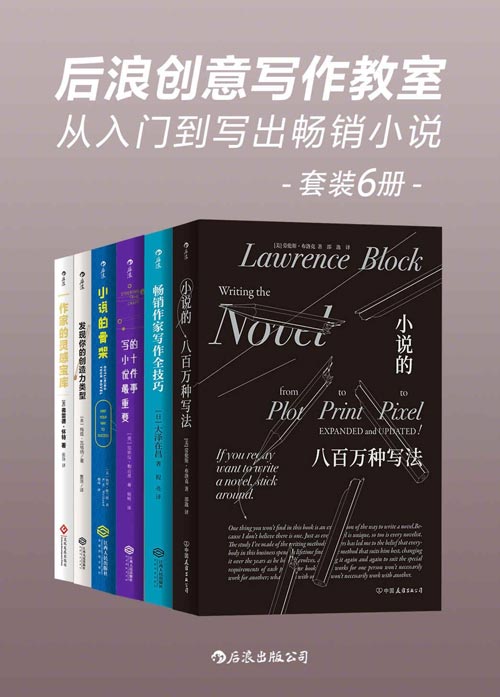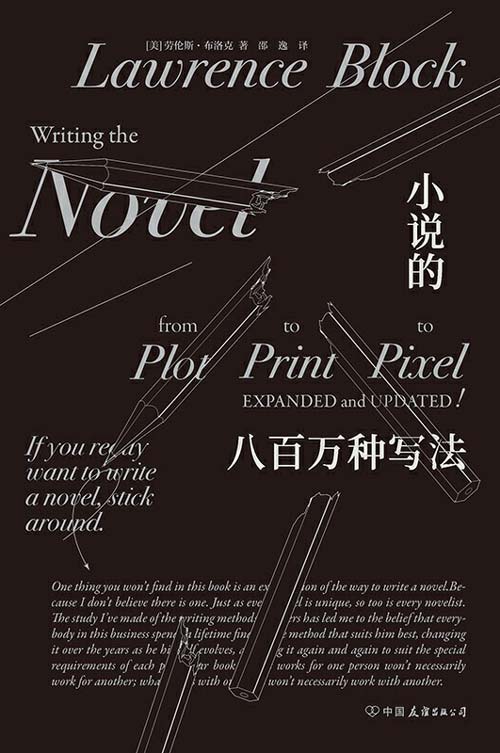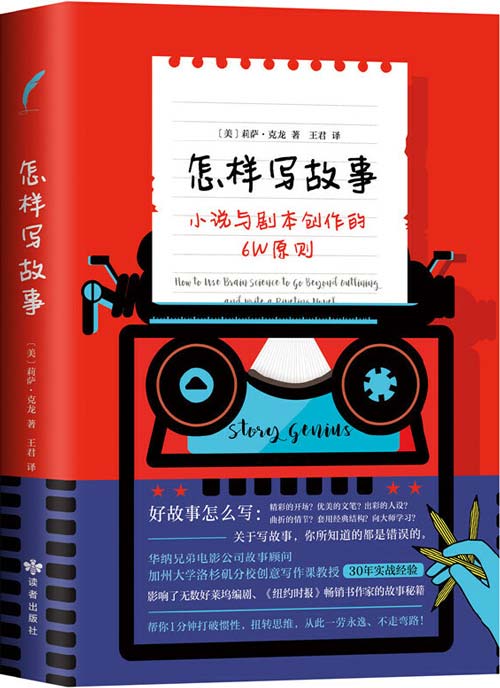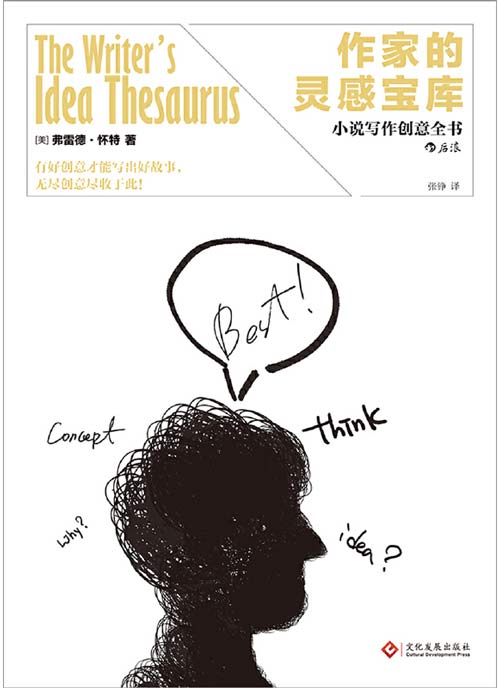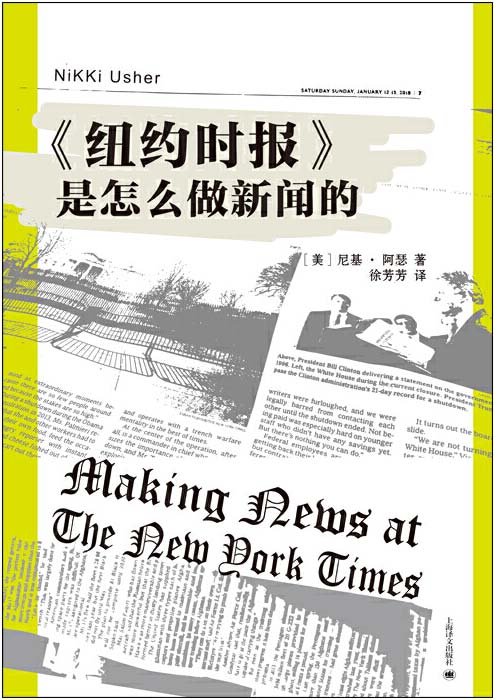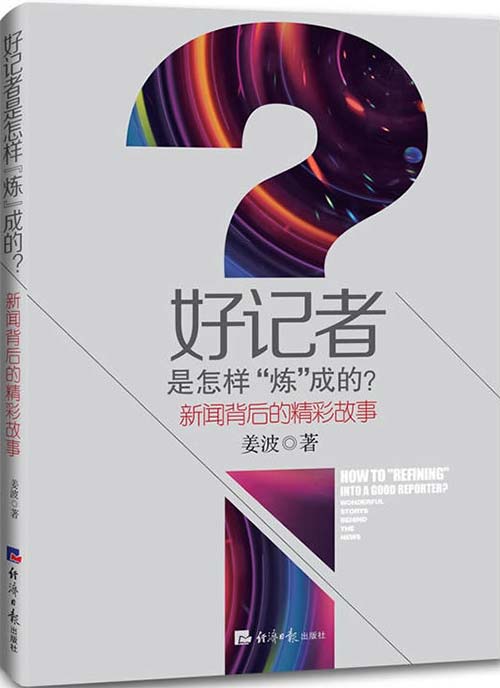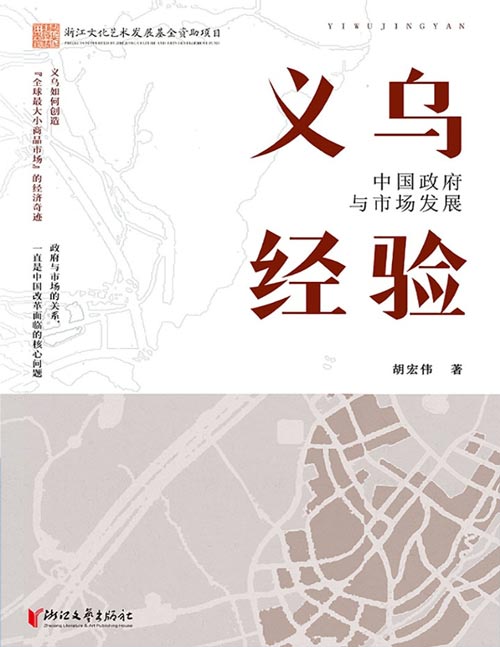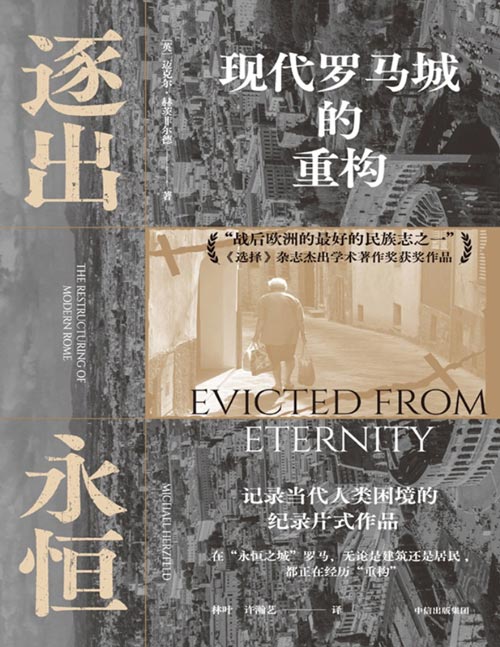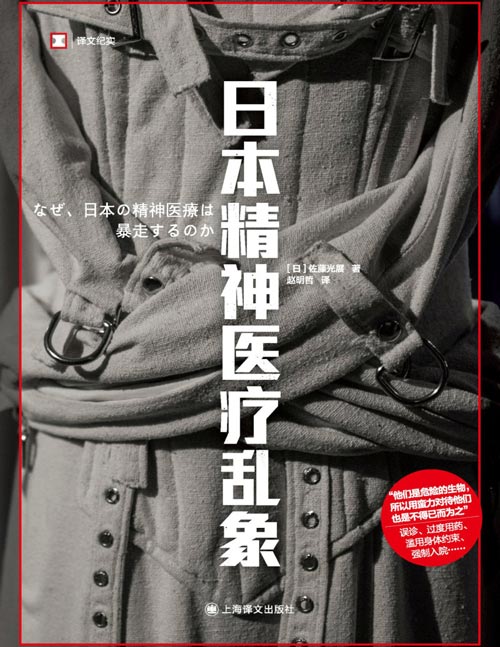编辑推荐
非虚构写作高手为读者讲述创作过程中动人心魄的故事。书稿本身就是精彩的非虚构作品,所选案例皆为关于行业内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披露名篇背后鲜为人知的创作历程!复盘经典报道现场,揭示转型大时代的叙事精。回答了读者最恳切想问的问题——何为非虚构?如何创作?
内容简介
本书凝聚了多位从业多年的著名记者、主编、作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成果。它以极具有吸引力的内容精华和大量案例去安排讲稿,且所选案例多数是行业内最精彩的非虚构作品。它结合作者自己的创作体验,对于各自最擅长的领域做了独到的剖析,并在文稿中回答了读者最恳切想问的问题;该书没有停留在如何写一个更好的稿子的技术层面,而是面向新闻传播学生,媒体从业人员和热爱大众文学的读者,尝试告诉他们如何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掌握非虚构创作的叙事精神要素。这本书不是用于应试的,而是尝试用丰富翔实的实战经验代替传统新闻传播教学的教科书,更希望成为广大学子和读者所喜爱的文学读物。本书由十余篇文章构成,从十余个不同角度解构一线记者的行业切片,展示出一个个写的漂亮、讲的有趣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作者简介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国际新闻传播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IJC)主任,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周逵副教授具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由其担任策划与撰稿的凤凰卫视电视专题纪录片《冷暖人生》在第45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电视纪录片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由其担任执行总编导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走进和田》获得2015年“五个一工程奖”。周逵副教授在国内外SSCI、AHCI、CSSCI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其译著《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获得2014年度文津图书奖。
目录
从玉华: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陈晓楠:我们就是在做“活着”两个字
卫毅:人物特稿就是去掉报告文学背后的金光
杨潇:从过度书写开始
赵涵漠:采访永不落空
袁凌:每一个字都是炼出来的
张鹭:坚守一线的调查记者不足百人
陈琳:极端环境的现场报道是对人性的挑战
林珊珊:人人都会讲故事
余楠:当我写娱乐圈时我写些什么
史晨:高价的体育、廉价的诗歌,谁之罪?
吉姆·沃尔夫:国际新闻是世界历史的初稿
刘子超:面包、黄油会有,还有诗歌和远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来自140位听众的话(代跋)
前言
失物招领
(代序一)
我小时候住在江苏省扬州水利机械厂。
这个厂建在运河边上,因为是水利机械,很多机器建好了以后就直接泊在河里,所以我小时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京杭大运河边。
1990年代的扬州作为一个中小城市,有许多国有企业,水利机械厂就是一所。城市里大部分孩子长大后不会外出读大学,一直在当地读书直至成为一名工厂的工人,如同我们父辈的生活一般。
作为一名工厂子弟,我们的童年和其他小孩不太一样,那时候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把吊车当作玩具开,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会坐在驾驶座把我放在大腿上,手把手教我操作高空大吊臂。元宵节的时候,厂里的所有小孩会推着纸扎的兔子灯去篮球场玩,兔子灯一倒火就着了,男孩子一看着火了,便灵机一动撒泡尿把火扑灭,小女孩在旁边吓得在那儿哇哇哭。大人则拿着板凳,吃好饭后散步到播放露天电影的地方,大家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等着电影放映。
运河边上住着许多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住在船上,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渔民家的孩子身上常常带有一股鱼腥味。于是欺负这些孩子便成为我们儿时的乐趣之一。他们吃饭有一个禁忌,不能将鱼肚翻过来,他们说这意味着翻船。一看到他们饭桌上窘迫不愿意翻鱼的样子,我们便会爆发出哄堂大笑。有一次,我们闲来无聊想要捉弄一个面黄肌瘦的渔民家女孩,于是一群男生在放学后把她逼到墙角拿胡椒粉撒在她脸上。这些当时在我们眼里的恶作剧如今看来不只是恶劣的玩笑,我每每想到此事,还对她心有歉意。
中午是厂里最热闹的时候,11点半前,工厂门口铁栏杆边上已经站满了人,很多双职工抓着栏杆翘首企盼中午回家给小孩做饭。
铃一响,门一开,所有人立刻蜂拥而出。那时候的米饭是用铝饭盒加热的,为了辨认出各个饭盒,我的小舅舅还用锤子和榔头勾出空心的名字来做标记。
对于职工来说,下班以后洗澡是个大问题,但托我父亲的福,小时候我都是去炼钢工人的澡堂子洗澡。炼钢工人每天都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干的是出汗最多最累的活,下班后可以免费用烧红钢水的热量去冲澡,这是属于炼钢工人的福利。然而这样一件好事却在我童年留下了阴影。因为如果要去洗澡,炼钢车间是通往澡堂的必经之路,那车间里到处都是烧红的铁水往下流,父亲每次都叮嘱我:别踩!那水得有几千度!我听着话战战兢兢地往前走,害怕自己真的会被那些流动的液体熔化掉。
由于是危险工种,炼钢工人的福利不止如此。一年365天处在高温环境下意味着每天都有高温补助,除此之外,最让孩子眼馋的就是上海产的金鸡牌雪糕,肥皂一般的大小,尽管包装简陋,但在炼钢车间上班的年轻人只要一拿出来,一群熊孩子便会蜂拥而上。
当时下班后的人们休闲娱乐活动并不多。我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去针织厂接活,那时的女工大都如此,她们往往挑灯夜战,在家里低着头在衣服上绣亮片或者串珠子赚一点钱,衣服上亮片绣多了就像鱼鳞一样,在灯光下泛出五颜六色的光。男人也不闲着,他们站在大马路边上等“活”。马路上的车经常抛锚,他们就冒着危险靠自己的手艺挣几块钱。
我身边的大人常常念叨生活真的太艰难,但无论多艰辛,扬州人总有一股积极乐观的劲儿,这从日常生活就能看出来。他们把酱油汤命名为神仙汤,扬州话的意思就是省钱汤,在母亲做工之前,她常常会给我们做神仙汤。
但即便是乐观,此时的我们谁都没有点破的是,改革的春风已经深入这座三线城市的传统企业。1980年代末对于我父亲和其他厂工而言,无疑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些胆大的人纷纷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
也就是那一年,父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调动工作。
父亲以前是汽修车间的工人,为了成功调动工作他费了不少脑筋。他早年参加过非洲建水坝的项目,回国后攒了一些钱,还带回了三大件和玩具。他给我的玩具是一个小机器人,能在地上到处跑,这个新奇的小玩具据说是父亲在法国转机的时候给我买的。但后来有一天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小机器人跑进了一个房间,从此再也没找到,这件事情让我难过了很久,父母安慰我说那个机器人跑回法国了。
直至后来长大,我回想起这件事问他们,他们才透露实情,原来这个玩具当初送给了厂长的孩子。除了那个小机器人,我的父亲还送了两瓶当时普通人家喝不到的可口可乐。不过可口可乐人家最后也没收。
而父亲终于成功转到了扬州电视台。
我的父亲当时有一项引以为傲的技能——开车。他曾载电视台陈导演的同事到我们家做客。我对外人总是充满了好奇心,第一次见到陈导演的时候心里还默默嘀咕着“他是女的还是男的?” 陈导演披着一头长发,头顶当时人人艳羡的电视台光环,有一辆泛青的上海轿,许多次都在我家门口的一条小路上扬尘而过。那一幕场景至今还有时在我的梦里出现,那条土路上一个男人,头甩在外面等人。
年仅12岁的我因为他的到来,小小的世界一下子被打破了。在那之前,我总以为,做一名厂工是我将来的生活。但当我第一次见到电视人,第一次见到上海轿,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自然,我迫不及待想要去看看外面的天地,冥冥之中,我与电视的渊源由此开始。
若干年后当我进入电视行业,再回到这个工厂大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印象中宽宽的路变窄了,高高的树变矮了,墙头的草长了几寸,砖瓦又掉了几块。老房子愈加斑驳,留在那儿的人越来越老,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老人还能操着一口吴侬软语认出我,说道你是逵逵啊……
公共厕所依旧还在那儿,那是我的第二童年阴影,还没走到跟前,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恶臭味。它和20年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墙上的油漆赫然写着的厕所二字“所”字已经掉了一半,成了“厕斤”。在这个标志旁还画了一个箭头,指向隔壁的“职工之家”。“职工之家”是从前的职工俱乐部,我上幼儿园的那会儿经常举办各类活动,父母还会和小孩一起跳舞。
如今“职工之家”空无一人,牌子还挂在那里,“家”字已经晃晃悠悠地倒下了。
一座江边小城、一间工厂、一群大院子弟,我的故乡消失在了命运的交错迷惘中。缝亮片的女工,修车的男人,运河边的渔船……这些故事逐渐模糊,飘着汽油味的童年慢慢消失,有些人就这样永远失去联系了。
他们如同历史人物,风化在你的私人记忆里,永不再回来。
如今在那条泥泞的土地上建起了扬州市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四周也已沧海桑田。我们谁都没有料到,90年代短短几年大环境的风水轮转把封闭社区里的人吹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此相见机会渺茫。原本都在那儿工作的三代工人到了第三代大都去了社会上谋职,厂子也越来越衰败,但由于它占地特殊,尽管年轻人都走了,它依然如同标本一样,亘古不变地伫立在扬州大桥边运河畔上。
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如果这些故事在我30多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们就会永远尘封在我心底的小角落里。那些关于国营厂风华正茂的记忆会逐渐模糊,终成为破碎的幻影。人往往生活在当下的时候,是不知道当下的,面对历史的时候,是不知道历史的。我们扮演的角色在逐渐成长,我们的身份在改制洪流里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个个故事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这不仅是我幼时模糊懵懂的记忆,也是那一代人绝望和希望并存的记忆。
“非虚构”也是如此。每个人的经历如此不同,回首遥望的时候,能不能理解自己的过往看的是个人的造化。我们庸庸碌碌度过一生,却可能对自己的人生一无所知。而“非虚构”这三个字的魅力就在于点醒我们,记忆是如此私人却又值得保留的东西,它建构在一代人的记忆之上,个体命运与这个时代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故事不被记录,就会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开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这是多么令人遗憾而痛心的事。
而这也是我想要出这本书的原因。
2016年8月
于京杭大运河最北端通惠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