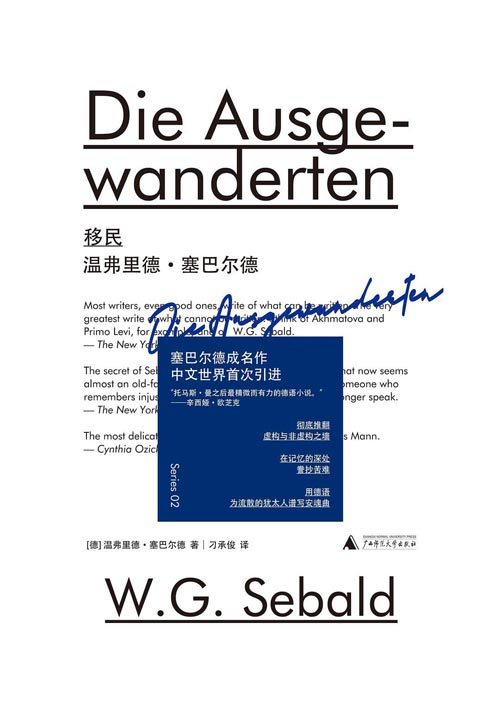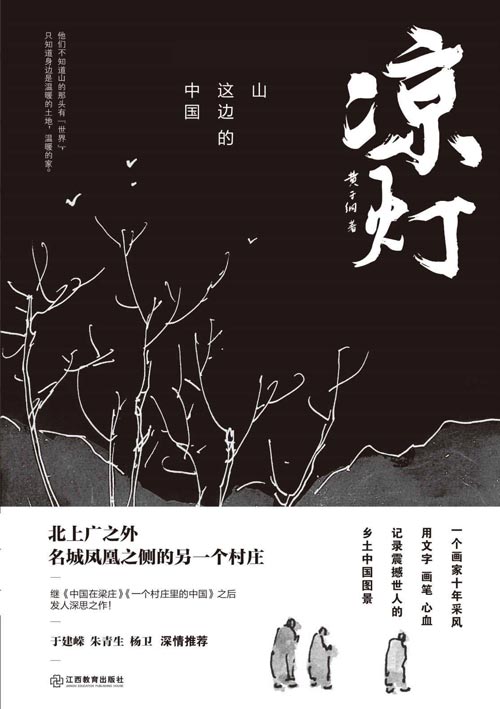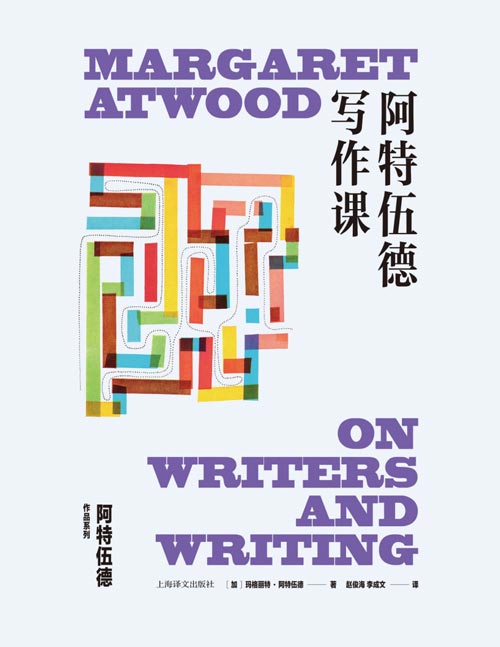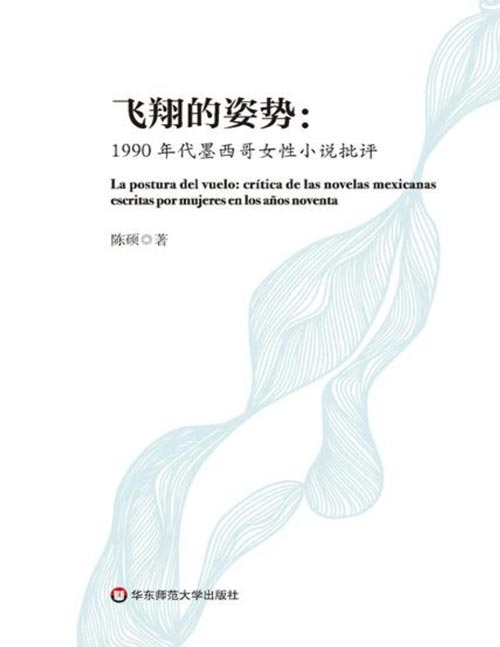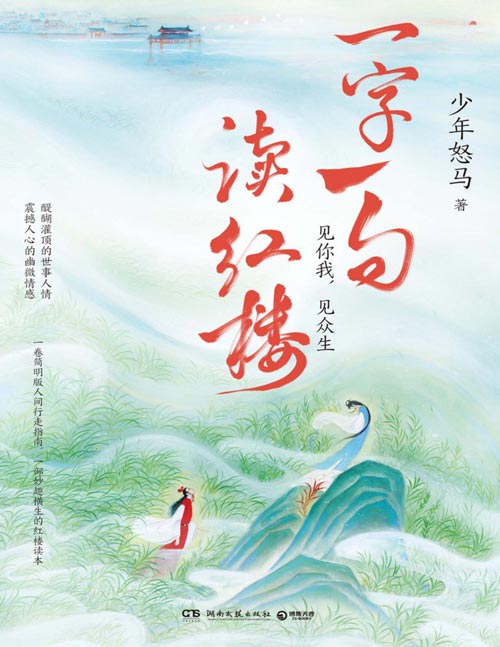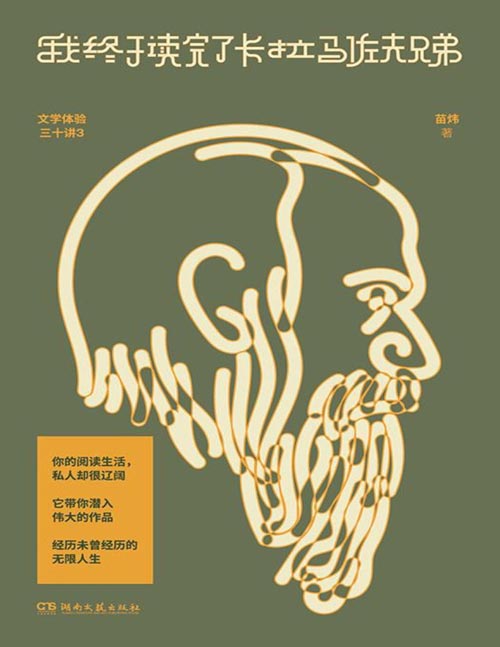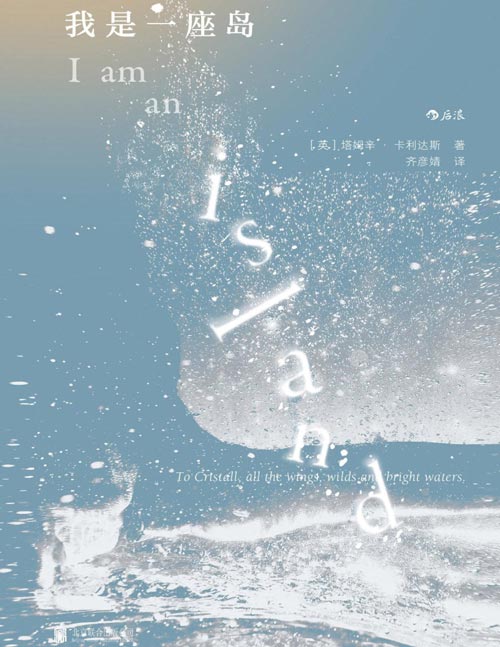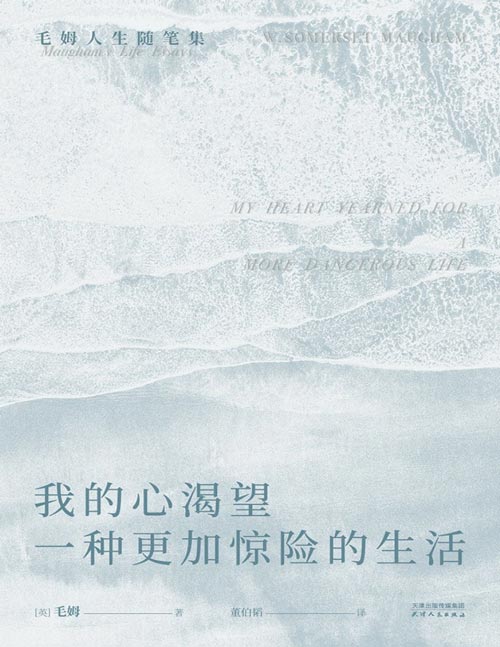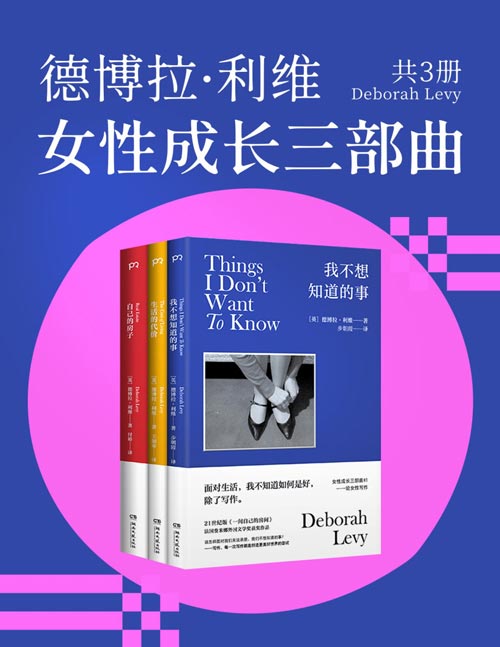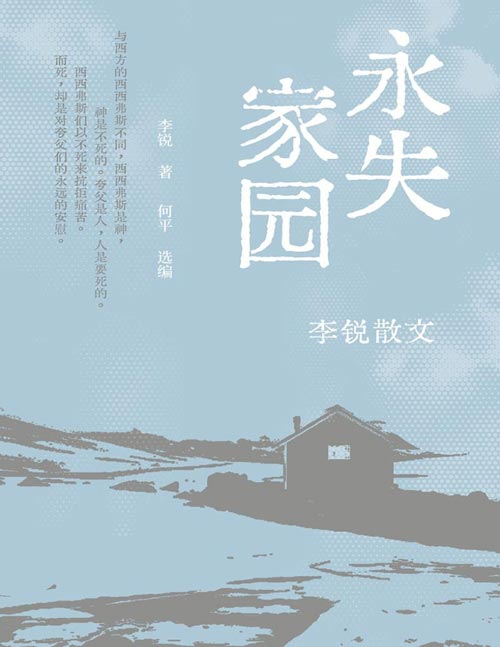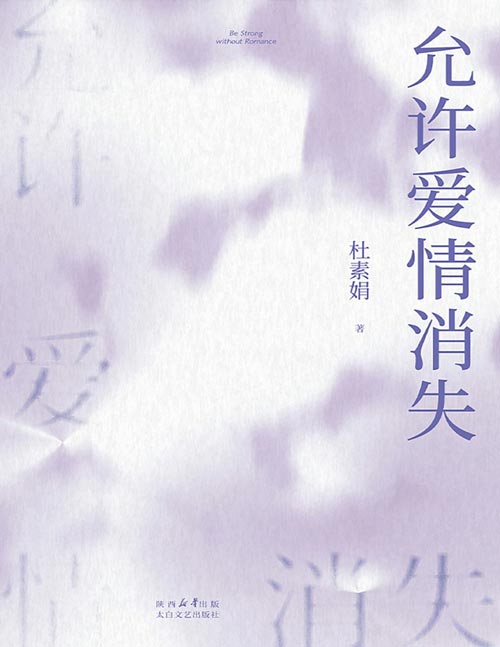编辑推荐
十九世纪英国传奇诗人、拉斐尔前派代表画家但丁·罗塞蒂十四行诗代表作;简体中文版首次面世,完整收录102首十四行诗;多幅诗人亲笔画作,全彩呈现;英汉对照、插图注释;典雅精装,独角兽文库
一首十四行诗,就是对某个瞬间的纪念。——但丁·罗塞蒂
1、作为画家的但丁·罗塞蒂,早已为中国读者熟悉,只要说起拉斐尔前派,人们总能*时间想到他;但作为诗人的但丁·罗塞蒂,始终未被中国读者充分认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国内此前尚未出版过他的任何诗集。现在,读者们可以通过《生命之殿》,一窥罗塞蒂十四行诗的迷人魅力。
2、全书无删减,完整收录102首十四行诗,中英文对照。译者对原诗作了详细的注释,方便读者理解和深度阅读。
3、书中配有罗塞蒂所作的多幅油画、水彩画和钢笔画,并附有对画作的解释以及对诗画的比照。
4、收录译者万字导读,从时代背景、文学渊源和文本角度对罗塞蒂的生平与诗歌艺术作了“百科全书式”的解读。
内容简介
但丁·罗塞蒂的十四行组诗《生命之殿》共有102首(含开篇),创作于1847年到1881年之间,在诗人临死前六月才最终定稿,代表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十四行诗艺术的成就,也是这个时期英国诗坛上的一部扛鼎之作。《生命之殿》充满了诗人关于时间、爱情和人生的感官印象,这一系列诗歌直接滋养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的唯美主义和颓废派创作。
作者简介
但丁·罗塞蒂(1828-188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拉斐尔前派代表画家。他的诗歌内省自观,远绝尘嚣,执着于探索人类激情的奥秘,沉浸于对爱、美与永恒的追求。他是十四行情诗高手,在戏剧独白和叙事歌谣方面,亦可比肩其文学前辈。他的作品以中世纪文学为滋养,上承浪漫主义,下应唯美、象征、颓废等潮流,观览他的诗作,就像观览一幅十九世纪英诗截面图。他的诗歌富有画意之美,很多作品或是为题画而作,或是配有他自绘的插图。
译者:叶丽贤,男,福建闽侯人,北京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助理研究员,译有《饥渴的想象:塞缪尔•约翰逊散文作品选》(2015年),曾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译文近20万字。
前言
译序
叶丽贤
1869年10月5日夜晚,伦敦北郊海格特公墓的一处家族墓地附近,忽然亮起了耀眼的火光。那是一座用枯柴架起的火堆,火堆旁是被挖开的墓穴,死者的棺材被抬了上来,就着火光,可以看到沉睡多年的女尸依然保存完好。一本灰绿色封皮的诗稿从棺椁中取了出来,上面还带着死者一绺金红色的头发。这份手稿里的诗作后来就成为撑起《罗塞蒂诗集》(The Poems, 1870年)的重要支柱。诗稿的作者但丁•罗塞蒂在七年前的葬礼上将它放在了爱妻的脸颊和鬓发之间,这是诗人对她的离去作出的最后祭奠,也是他付给卡戎(Charon)的一笔通向“死亡”的费用。七年以后,罗塞蒂向“死亡”要回了这笔通行费,将这一枚枚“钱币”重新投放到阅读市场中,在与读者灵魂的“交易”中,他的诗集和诗名才流传下来,直至如今。
诗稿重见天日后不久,罗塞蒂就开始誊抄和修改其中的诗作,并加入新的作品。1870年,《生命之殿》作为《罗塞蒂诗集》的一个单元发表,当时共收录50首十四行诗。爱、生命、死亡以及对诗名的追求,既是《生命之殿》的关键主题,也是推动《生命之殿》面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罗塞蒂诗集》的出版在当时的文坛和批评界引起巨大轰动。1871年罗伯特•布坎南(Robert Buchanan)发表匿名文章《肉感诗派:D•G•罗塞蒂先生》,批评《罗塞蒂诗集》(包括《生命之殿》)对“纯粹的肉体感动”的描写,指责罗塞蒂将“肉感”(fleshiness)抬升为诗歌和绘画“最突出、最崇高的宗旨”,从而引发众多书评人的回应和争论。罗塞蒂当年12月在《当代评论》中发表《鬼祟的批评学派》一文进行自我辩护。这场维多利亚时期最有名的文学争论持续时间长达五年,将罗塞蒂推到风口浪尖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他作为诗人的知名度。接下来的十年,是罗塞蒂深受失眠、抑郁、幻听、药物上瘾、精神崩溃困扰的十年,是生命仍与冬日的死枝相纠葛,一个个“自我”被残杀和埋葬却等不来新生,“爱”、“诗乐”和“艺术”都要相继死亡的十年。但简•莫里斯这位“真心女人”(true woman)的相伴相知为他的情感生活和文艺创作注入新的激情。尽管罗塞蒂与简的火热恋情到1874年时就已结束,但这段感情催生了《生命之殿》里众多歌颂美和年华、爱意缱绻动人的诗篇。第12首《情人的漫步》和第19首《沉寂的午后》就属于这个时期两首情意深浓、想象优美、语言修辞富有表现力的作品。1880年到1881年间,罗塞蒂再次感到自己内心澎湃的诗情;在挥笔书写新篇时,他着手准备出版新的诗集。在罗塞蒂的出版计划里,有一项尤为重要,那就是扩展1870年版的《生命之殿》;增扩后的十四行诗篇目要比原先多了一倍,共计102首(罗塞蒂删去了曾引发热议的《婚眠》这首诗)。从传记的角度来看,1881年版的《生命之殿》是由两段缠绵悱恻的恋情所主导;其中一段的对象是伊丽莎白,她已经亡故,被供奉在想象的天堂里,而另一段的对象则是简•莫里斯,她将诗人从天上带回到现世的生活中。
《生命之殿》中诗歌的排列并不是以创作时间为序,而是经过罗塞蒂精心的设计。这部诗集大体呈现了诗人的心灵由“爱”向“死”最后又复归于“爱”的历程。诗歌开篇的“爱”是居于高天、完美自足的理念之“爱”,后来它堕降到人世间,在肉身的束缚、社会关系的限定、时间的消磨中,慢慢蜕化,被生离死别所左右,丧失了它神圣的救赎功能。与此同时,诗人以“爱”为核心的人生信仰,以“爱”为基石的价值体系,逐渐动摇,趋于崩毁。可以说,《生命之殿》是一部关于“爱”的堕降神话。这个神话由两大部分组成,即《青春与蜕变》和《蜕变与死亡》。标题中的“蜕变”除了指“爱”的蜕化之外,还指向这部诗集所呈现的一条轨迹,即从满是“繁花与深林”、远离“聚散无定,离合悲欢”的庭院转向见证了人类世代更替、断枝腐根到处可见的园林,从两人“亲密相伴”,拥抱着“无言的时光”的初夏草丛转向“失落的流光更续着失落的流光”的秋日树林,从回响着“和鸣谐奏、美妙悦耳”的爱曲的小楼转向“只有嘲弄的风吹过满地的秕糠”的寓所,从“飘溢着柳香,将天空深深拉到……心怀”中的爱溪转向要从“死亡”手中饮下“苍白浪花”的遥远河滨,从以“爱”作为“夜里的辉光,午时的凉荫”的宁谧“港湾”转向一路上只有浓厚的“长云”与“长林”相伴的孤独旅程。总而言之,这一条轨迹是从伊甸园的天真与幸福向炼狱式的痛苦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在《青春与蜕变》中就已开始,到《蜕变与死亡》时愈发明显和激烈。与《青春与蜕变》相比,《蜕变与死亡》所关注的心灵面向更为深广,情感基调也更为暗沉。它收录了罗塞蒂一些论述情感或想象与诗歌的关系,回顾自己的艺术志向和追求历程的诗篇,虽然它们与“爱”或“蜕变”主线没有直接关联,却构成了对《生命之殿》其他诗歌的注解和评说。
《生命之殿》中的诗歌布局是罗塞蒂在1880年到1881年间,即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设计的。他在晚年重新审视这些业已面世或尚未发表的诗作时,心中必然别有一番滋味,甚至还可能发现这些作品与自己人生从未有过的关联。他对这些诗篇的安排客观上也影响了它们内在意义的生成。第91首《共有的丧痛》写于1854年,当时但丁•罗塞蒂年仅27岁,威廉•罗塞蒂认为这首诗表现的是他兄长在选择以绘画还是诗歌为毕生追求时的犹豫和挣扎。这样的阐释也许无法完全涵盖1881年罗塞蒂重读此诗时的理解。如果将《共有的丧痛》与第86首《失去的日子》、第97首《重题》、第98首《他与我》等邻近的诗作联系起来,这首诗的主题就超越了年轻人在选择事业时的矛盾内心,而指向了“自我的分裂”这个一直萦绕在晚年罗塞蒂的生命意识中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诗中“回街曲巷”和“路边落满尘土的小酒馆”就成为缺乏明确目标和行动意志的人生旅程的隐喻。《蜕变与死亡》中还有一些诗篇,如第65首《枉然的领悟》、第67首《界标》、第68首《幽暗的白昼》、第69首《秋日的懒散》、第70首《山头》、第86首《失去的日子》,同样都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即罗塞蒂正值二三十岁时。在1881年版《生命之殿》中,这些诗作的内涵也同样可能被罗塞蒂的人生阅历和诗篇布局所重新塑造。
严格来说,《生命之殿》并不只是一部十四行诗集;用罗塞蒂自己的说法,它其实是“十四行组诗”(sonnet sequence)。在这种诗歌结构里,每一首十四行诗都蕴含一个完整的思想,自成一体;同时,每一首十四行诗都属于诗歌阶梯中的一级,它与其他诗作构成相互映射、补充或阐释的关系,将诗人的思绪沿着某种轨道推向它的终点。结合主题来看,《生命之殿》属于“爱情十四行组诗”(amatory sonnet sequence)这一至少可追溯至14世纪彼特拉克的诗歌类别。19世纪中后期,尤其后三十年,是这类诗体的创作爆发期,出现了布朗宁夫人《葡萄牙十四行诗集》(1850年)、乔治•梅瑞狄斯的《现代爱情》(发表于1862年,梅瑞狄斯将十四行诗的形式改造为由“彼特拉克四行体”构成的十六行诗)、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无名的女子》(1881年)、亚瑟•西蒙兹(Arthur Symons)的《海上之星》(1884年)等。处于这股创作风尚的一些诗人,如布朗宁夫人和梅瑞狄斯,将原来歌颂男女私情的十四行诗移植到家庭生活中,转而去表现夫妻之间的深情或“正当”的婚姻家庭观。《生命之殿》中的“爱情”也一样,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逾越合法婚恋的界限。罗塞蒂在回应布坎南对《婚眠》一诗的批评时强调的一点就是:这首诗表现的是夫妻肉体的欢爱(第6行的意象“缔结良姻的花朵”对此有所暗示)。尽管《生命之殿》中的部分诗篇是基于诗人与简•莫里斯的情感关系所作,但罗塞蒂在这些作品中极力淡化了男女私情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在1881年版《生命之殿》中,带有“肉感”色彩的诗作所占的比重其实很小,主要集中在《青春与蜕变》的开头部分。即便在这些“活色生香”的诗作里,罗塞蒂也一再强调或暗示身体的愉悦只是灵魂契合的一种表现,人光有“激情的澎湃”并不够,内心总会生出“一种更深的渴求”,只不过这些诗篇就像罗塞蒂笔下的莉莉丝一样,太过耀眼闪亮,读者一不小心就坠入她的丝网中,“心灵、身体和生命”完全沉沦,而忘了他笔下还有一位“令人敬忌”,同时也化作人类生命气息的“‘美’之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