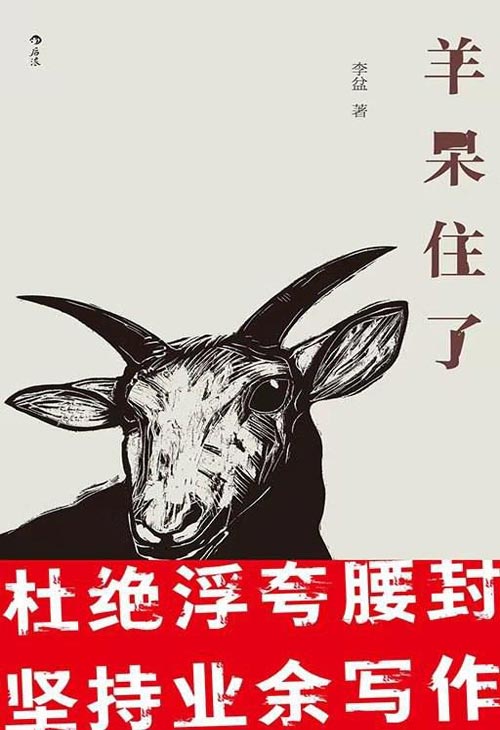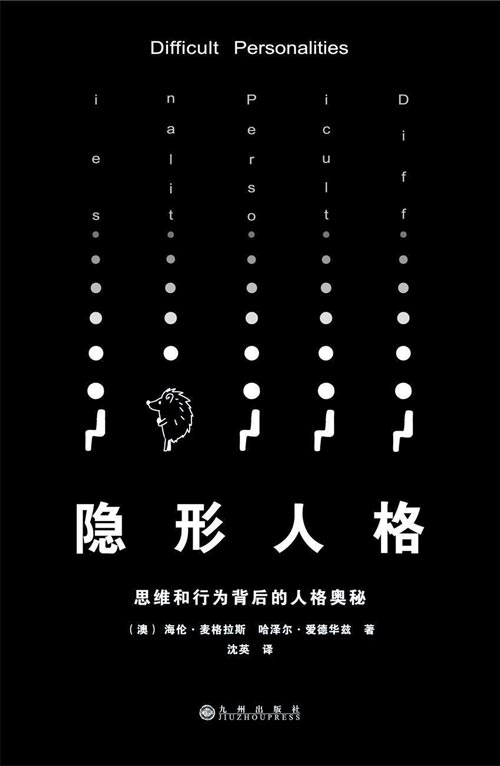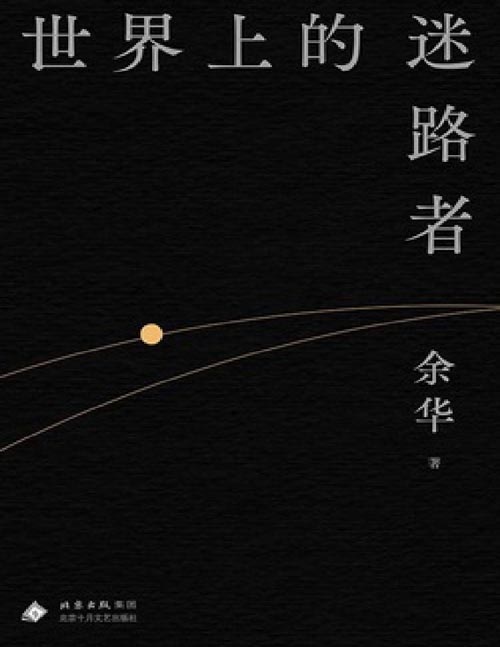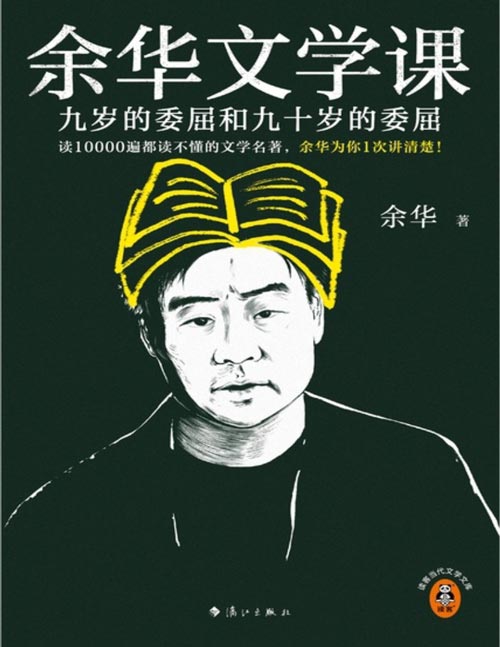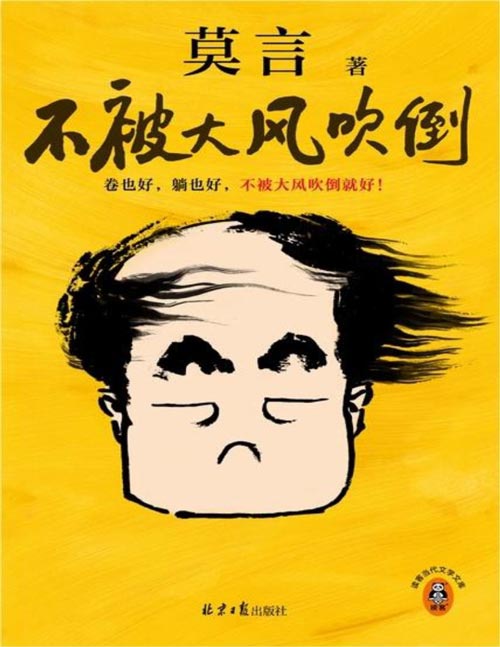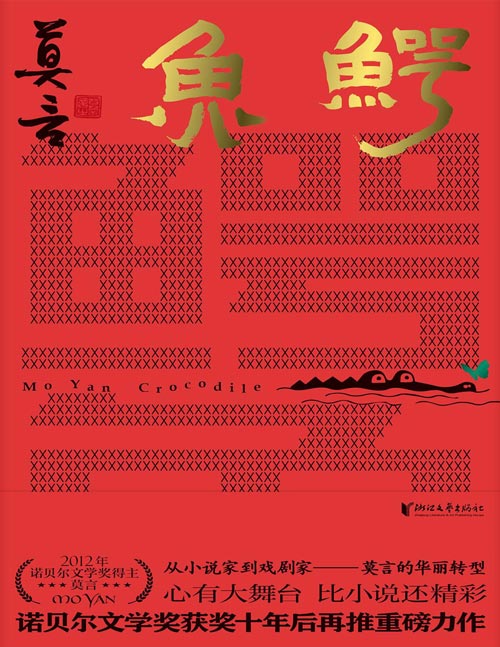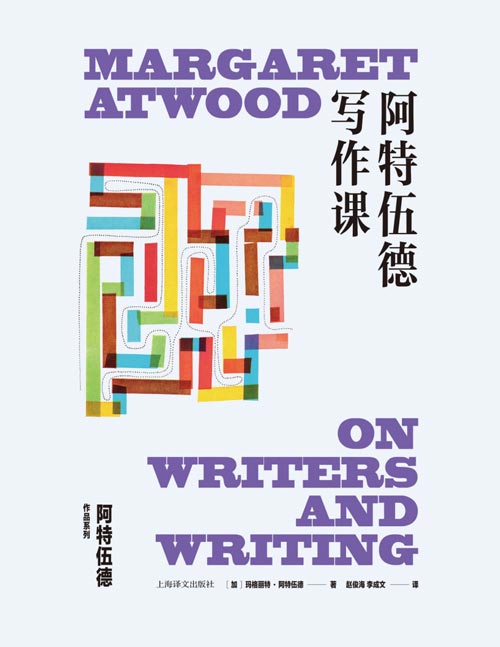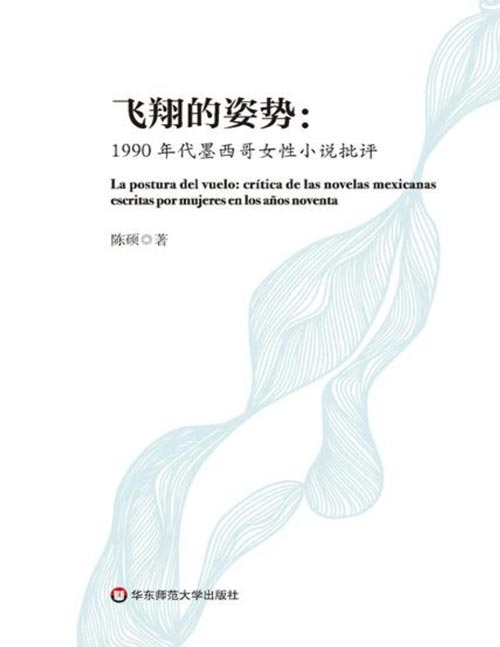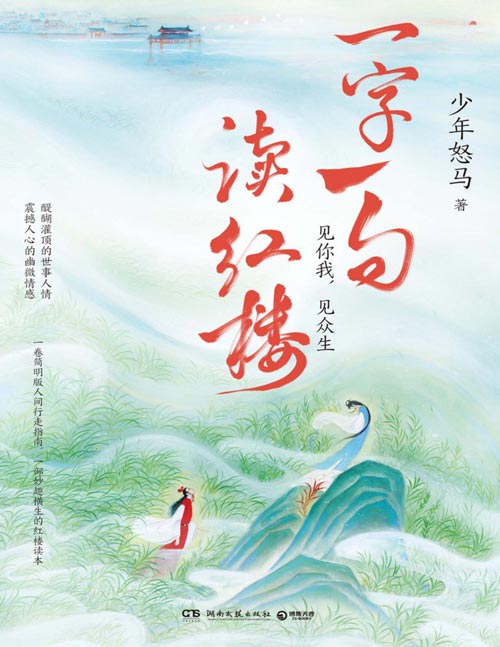编辑推荐
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读懂一位文学大师
为什么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名至实归的?
余华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
为什么王安忆的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
内容简介
八十年代是什么?《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写道: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八十年代,是朱伟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的年代。在此期间,他相继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
本书是朱伟三年阅读和写作的结晶,他逐一重读了活跃在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条分缕析,系统解读了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10位标志性作家的作品,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
作者简介
朱伟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微博粉丝225万。
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任文艺部编辑。
1983-1993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
曾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1988-1989年在《读书》杂志撰写《*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因爱好古典音乐,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代表作:《考吃》《有关品质》《微读节气》《四季小品》等。
前言
自序
我一直说,此生幸运,是在还年轻时,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学年代。我的八十年代始于1977年冬进《人民文学》当实习编辑,那时我是个户口在黑龙江的知青。我要感谢把我引进《人民文学》的,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是他带我走上的编辑工作岗位。
我一直说,我在八十年代的幸运,是因在《中国青年》遇到了时任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又因为王蒙而回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因为《人民文学》解决不了户口问题,才进了1978年正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有幸经历了《中国青年》复刊事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朝气勃勃的《中国青年》集体中的一员。回到《人民文学》,是因为王蒙说:“你要做文学编辑,还是到《人民文学》吧。”我就随他回到东四八条,亲历了《人民文学》辉煌的1985、1986,成为1987年一二期合刊的当事人。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了生命中的一段坐标。八十年代是什么?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在网上到处流传——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黄子平说,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李陀坐两站路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进去的;是可以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我还清楚记得,早晨我骑车去阿城家里,他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去,他则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
整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履迹,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留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因此,我的八十年代记忆中,满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印象。那原是我太太娘家以很多张工业券买下来的产权,结婚时我太太从家里骑过来,成为我们小家的财产,因是男车而成为我的交通工具。我骑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胡同,避开警察,送儿子去幼儿园。冬天的寒风中,那双小手紧紧抓在车把上。一次他的脚没蹬住竹椅,卷进了前轮,我俩一起被紧急制动摔出去,他的脚卷在轮里,脸被冻硬的路面蹭破,幸无大碍。骑自行车的冬天总是格外刺骨,下雪化过又结上冰,路上就是纵横交错的一道道浅浅深深的冰坎。我记忆深刻是,那一个夜晚我骑车从白家庄去和平里,给影协的陈剑雨送刚写完的《红高粱》的电影剧本初稿。那时的自行车已是老年,处处毛病了:车把是松的,每在冰弄里遇到坎,随时都像要摔倒,但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过去。还有的骑自行车记忆,则是编《东方纪事》时,我骑着它,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陈平原,那是八十年代末了,居住范围扩大,相距已经远了,骑在自行车上,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已经觉得累了。有时,骑着骑着,睡着了,一个激灵,吓一大跳。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儿子上补习班停在楼下,它终于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轻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我曾在博客中开始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我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结果,开了个头,就因为还在岗,工作繁忙,放下了。退休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邀我写专栏,他希望我写写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作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尽管有些作家还未写到,也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有人说,这其实是一部,一个个人经历的,八十年代文学史。我想,也许,再花几年时间,涉及的作家更广泛些,才能形成系统与规模。且,一部文学史,还必须对八十年代各阶段社会背景的烙印作出反应,因此,这本书,只能算一个开端,一个基础。
总是心有余力不足。时间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能完成的总是有限,这是我一直的嗟叹。
是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