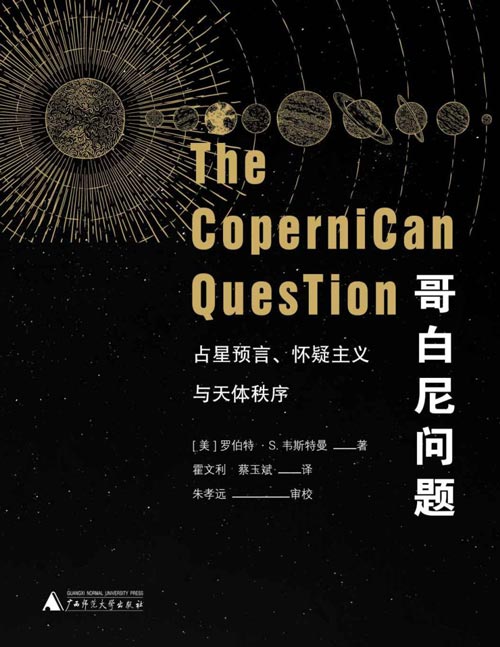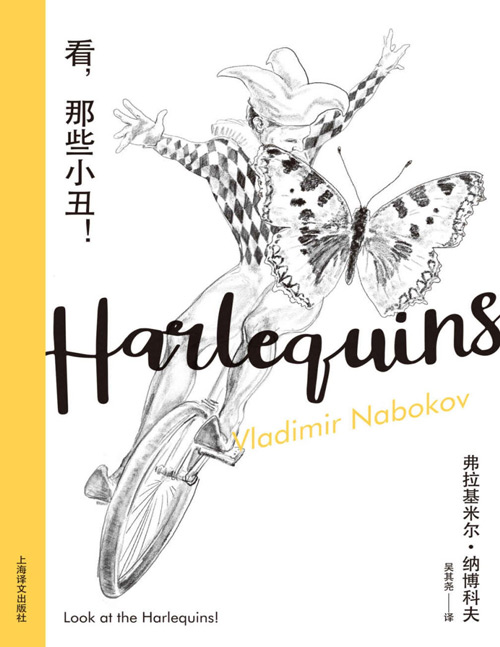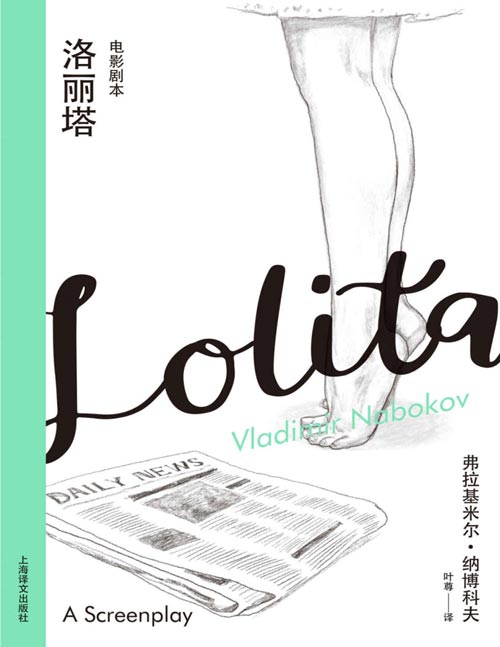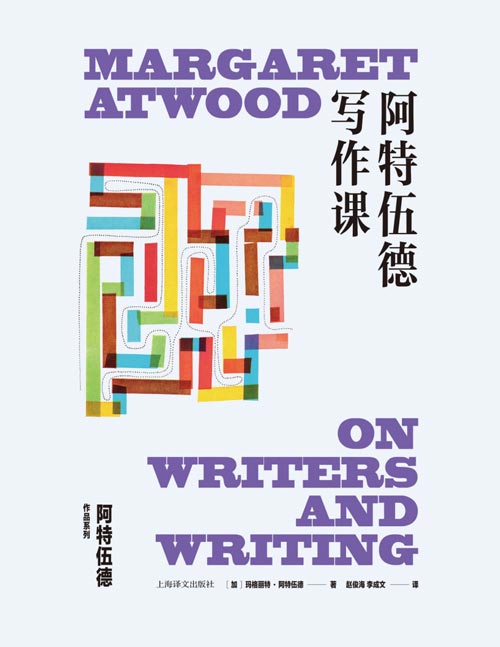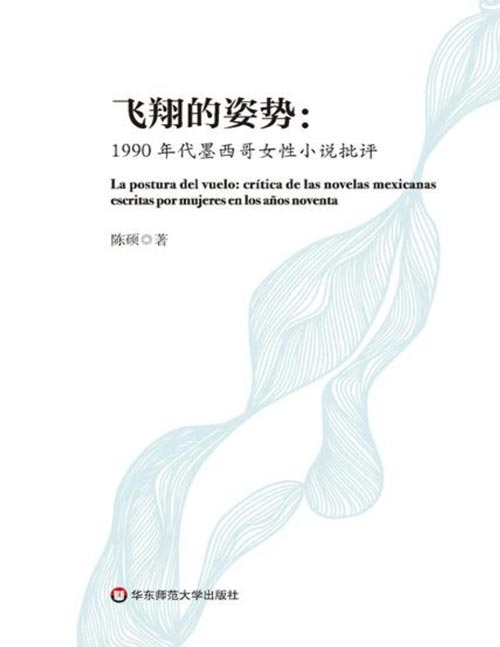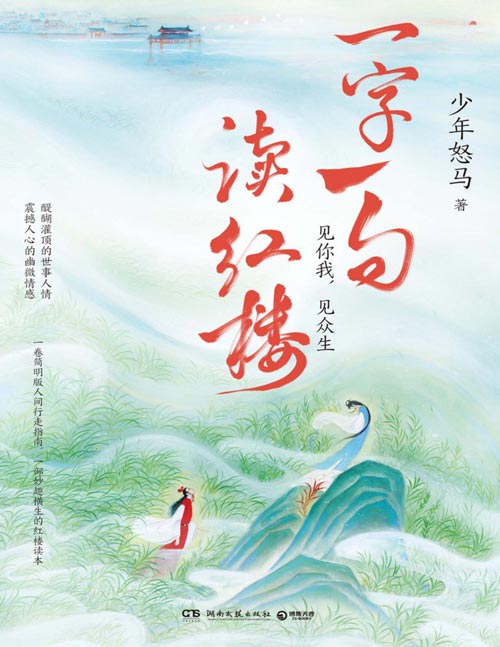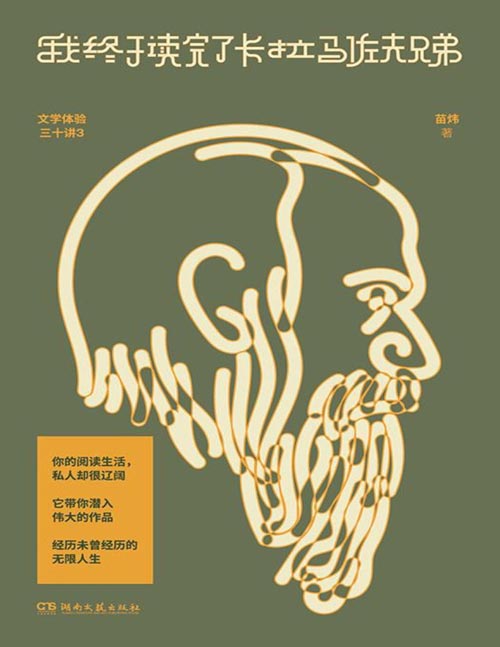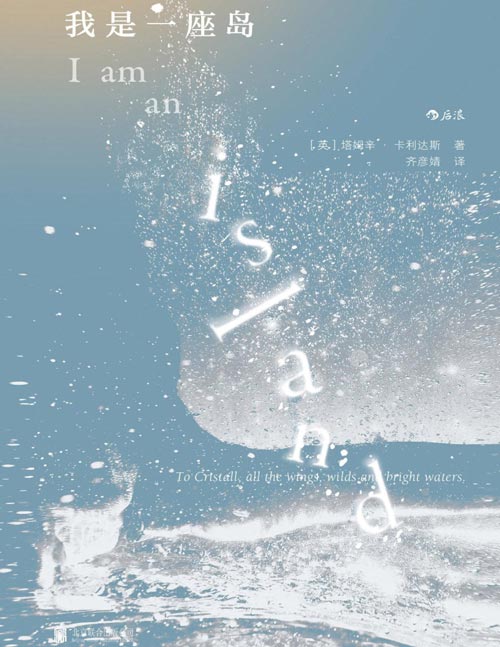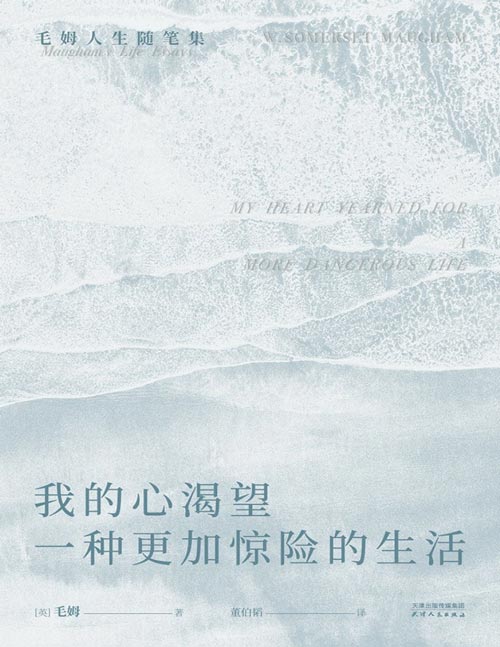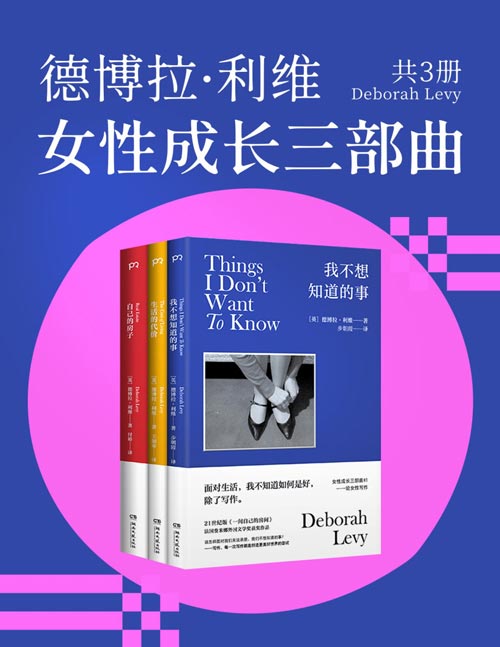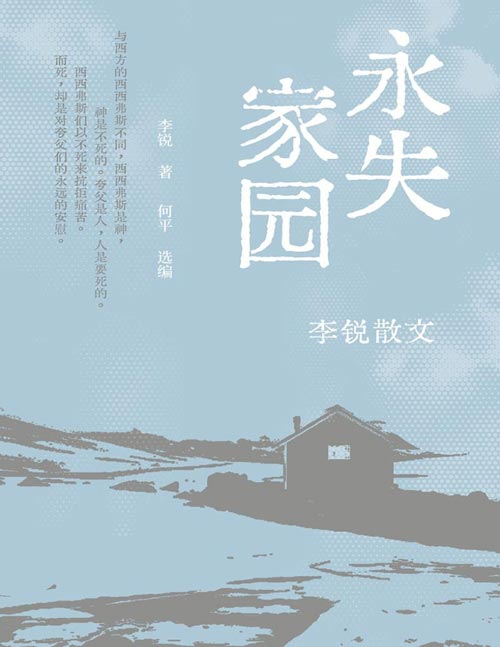内容简介
《独抒己见》是二十世纪公认杰出的小说家、文体家纳博科夫的自编文集,以《巴黎评论》《时代》《纽约时报》《花花公子》、BBC电台等知名媒体的采访为主体。22则访谈,11封致编辑的信,14篇文论,勾勒出鲜明而坚定的自我肖像。不同于其他小说作品,《独抒己见》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自述;江湖上流传的独具纳式风格的“毒舌”经典语录,大多出自此书。纳博科夫面对着媒体提出的种种刁钻问题,如书名“strong opinions”所体现的,提出一系列坚定见解,谈及生活、文学、教育、电影以及其他种种主题:“洛丽塔”如何险些付之一炬;对蝴蝶怎样迷恋一生;什么是心目中*理想的旅行方式;翻译和创作艺术的终极标准是什么……他毫不理会那些读不懂他作品的庸众,乐于宰杀那些他不认同的文坛神牛。读者可以藉由这些火花四溅的文字,读懂纳博科夫,踏上他脑海中那座迷人、险峻而富于挑战的精神岛屿。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前言
弗拉基米尔 • 纳博科夫
我思考时像一个天才,书写时像一个优秀作家,说起话来却像一个不善言辞的孩子。我在美国的学院生涯中,从一个不起眼的讲师到堂堂正教授,从未不事先准备好打印稿就对众宣讲,在灯光明亮的讲台上眼睛也从不离开讲稿。我接听电话时的语无伦次会让打来长途的人从流利的英语改用可怜的法语。在聚会时,要是我想讲个有趣的故事来让朋友开心,那必定讲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就是在早餐桌上对我妻子描述的隔夜梦也只是一份初稿。
因而,人们不应请我做什么访谈,如果“访谈”意味着两个正常人之间的一种闲聊。先前至少试过两次,有一次,还用了一台录音机,但当磁带倒回去时,我赶紧收住笑声,我明白,此后我再也不会重演这类角色了。现在,我小心翼翼,以确保做访谈时气定神闲,悠然自得。采访者的问题必须书面递交给我,我进行书面回答,发表时一字不差保持原样。这就是我接受采访的三个先决条件。
然而,采访者希望拜访我。他们希望看到我摆在稿纸上的铅笔、彩绘灯罩、书架和躺在我脚边的白色老牧羊犬。他们觉得需要有助于营造轻松气氛的背景音乐,需要能够被记住的丰富多彩的细节,即使并不是真的草草记下(“呐,灌一口伏特加,咧嘴讥讽道——”)。我是否想取消这种故作轻松的笔调?是的,我想。
护发用的某种优质洗发液,实际上是一种难看的乳化剂。制造商通过添加绿色素使之变得诱人——在传统美容业,绿色会让人联想到春天的清新,联想到松树林、翡翠、树蛙,等等。然而,你必须把瓶子用力晃动,里面的溶液才会呈现绿色;而如果不晃动瓶子,那我们所看到的,上面是一英寸厚的绿色,而底下则是未变化的、天然的乳白色液体。在我看来,使用前不晃动瓶子是一个原则问题。
同样,涉及印刷后的访谈效果,我并不在意表面文章,而只看重实质的东西。我的文件中存有约四十份好几种语言的访谈录。本书只收了一些英美人士所做的访谈。有几份访谈不予收录,是因为它们出于一种糟糕的炼金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晃动;我诚实的应答与炮制者添加的人情世故的虚假色彩搅和在一起,以致根本无从分辨。另有几份我轻而易举地撤去了那些不无好意的小摆设(还有那些花哨的新闻噱头),这样,就逐步剔除了每一种自发性因素,以及所有与现场交谈相似的东西。访谈最终就变成差不多是一篇段落分明的文章了,这也正是书面访谈应有的理想形式。
我的小说很少给我机会来表达我的私见,因而,我偶尔也欢迎迷人的、彬彬有礼而又聪明的来访者提出一大堆的问题。本书中,在访谈录之后是几封给编辑的信,它们就像律师行话所说,“不言自明”。最后是一组短文,除了一篇,其余都是在美国和瑞士写的。
斯文朋对“一伙蜕变为拙劣批评家的恶意而又丑陋的蹩脚诗人”有过敏锐的评价。一九三○年前后,这种奇怪的现象也是巴黎俄国侨民文学小圈子里的典型状态,那时,蒲宁、霍达谢维奇,以及其他一两位杰出作家的美学思想尤其受到来自以不同方式“介入”的痞评家(criticules)的恶毒攻击。在那些年里,我巧妙地嘲讽那些艺术的诋毁者,为我的文字激起那个帮派的恼怒而欣喜不已;但是,今天要把我那些为数不少的旧文从艰涩的俄语译成迂腐的英语,再对文中那些旁敲侧击和行文策略的妙处做一番解释,无论对我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一件提不起兴趣的苦差事。唯一让我自己有个例外的是 《论霍达谢维奇》那篇文章。
因此,眼下这本我偶尔为之的英语文选,剪去了它长长的俄语影子,似乎反映了一个远比“弗• 西林(注:纳博科夫早期写作的笔名。)”更讨人喜欢的形象,而提起西林,会在侨居的回忆录作者、政客、诗人和神秘主义者那里引发复杂的感情,他们仍记得我们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巴黎的遭遇战。如今一种更温和平易的性情渗透在我对自己观点的表述中,尽管这些观点十分强硬。理应如此。
1973年于蒙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