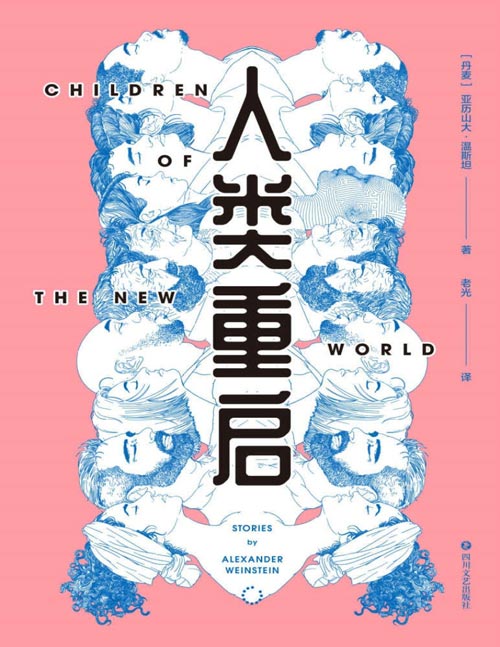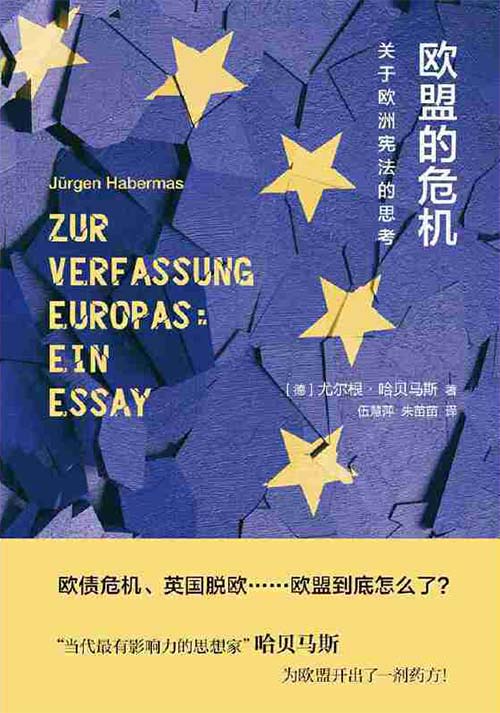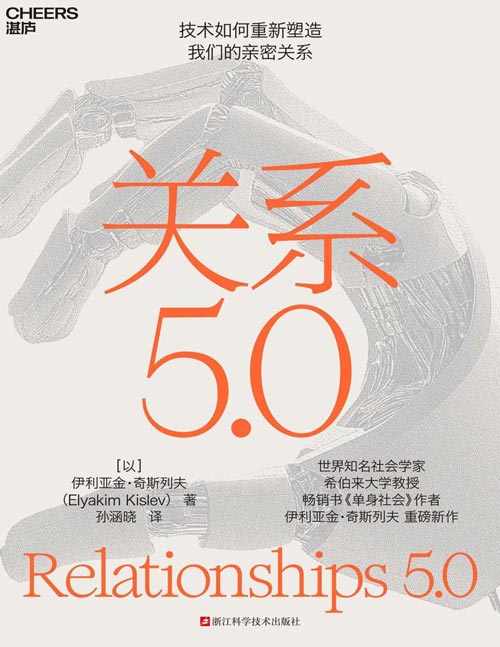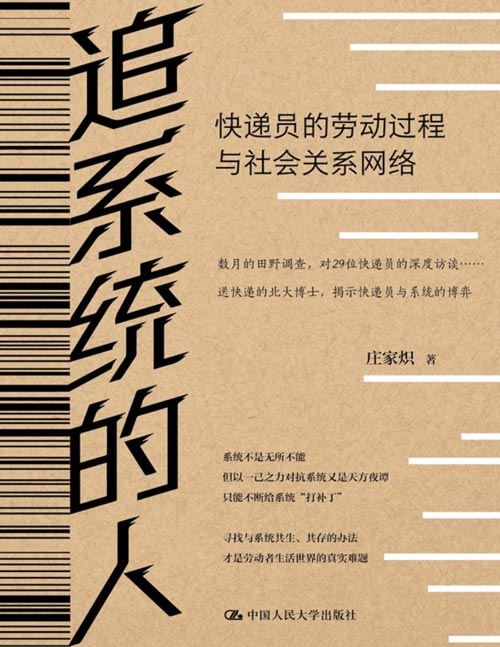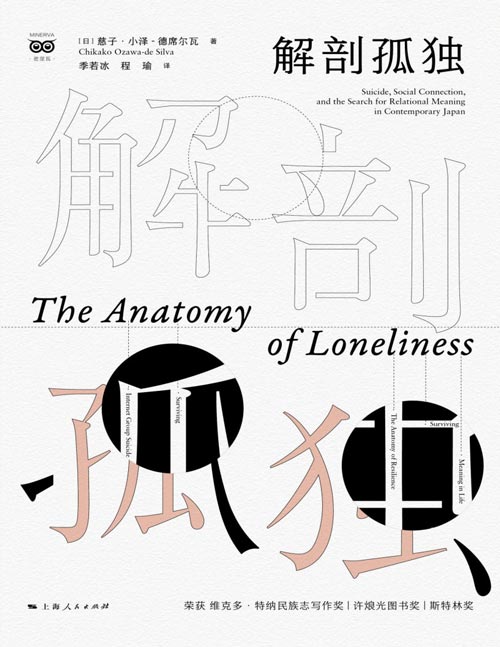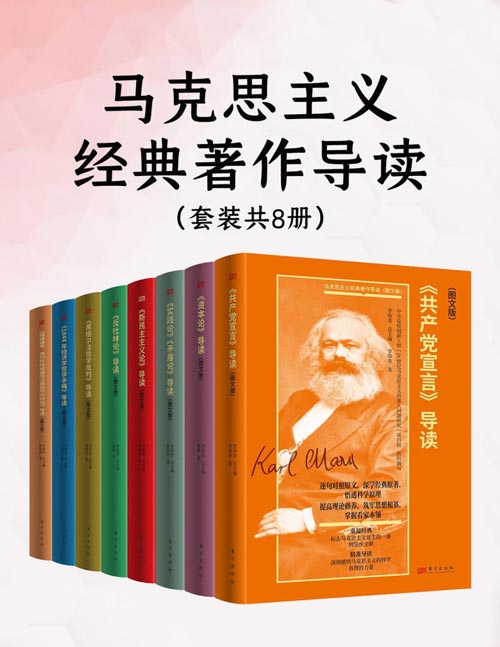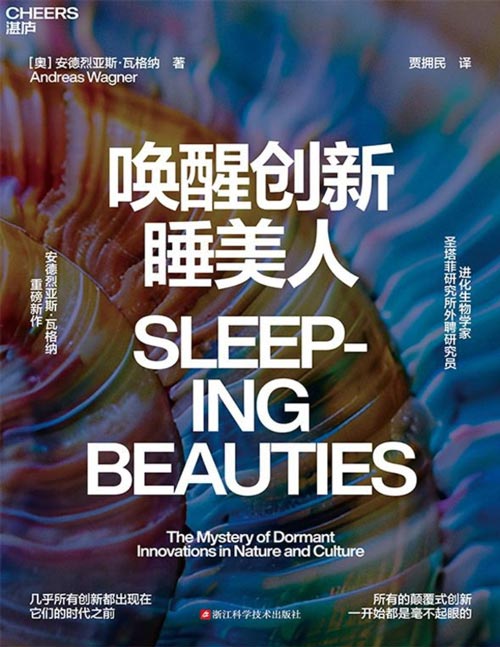编辑推荐
暌违逾十年,苏力教授全新力作《大国宪制》!本书将展示,我们的先人,在这块后来才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活下去,为活得稍稍好一些,以什么样的智慧或者“极精练的愚蠢”,一代代合作、演进和积累,造就了如此的中国。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宪制作为人类历史上持久存在的制度经验,有其自己的逻辑和合理之处。但近年来社科领域特别是法学领域,对于中国自己的制度研究较少。作者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历史中国的宪制经验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深度总结,揭示了历史中国千年传承、具有强大活力的原因,并力图阐释中国在制度文明上独有的贡献。本研究从历史中国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核心政治问题出发,逐一阐释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构成制度,以及军事制度、官僚体系、经济制度等,从而重构了历史中国的制度图景。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祖籍江苏,1955年愚人节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1970年)从军,再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员军人进了北大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起任教北大法学院至今。先后独立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个人独著、文集和译著20余种。
前言
读书一直杂乱,早就想依据中国历史的常识,顺着读书的触动,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国家制度视角,也即宪制的视角,展示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家之构成也即宪制的固有理性和正当性。关注制度,是实在的,但也关注其中的大小道理,因此也是规范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其实又是两者的整合。这才是我认为好的、有用的并可能让人举一反三有所觉悟的法律/法学著作。我曾打算名为“思想中的法律史”。但不可能完整或全面描述中国宪制,也就放弃了,只是依据我的有限知识和不全面的思考,展示为什么这些在我看来对于中国非常重要的制度或实践会发生,无论后人如何评判,尤其是不论旁观者或上帝视角下的善恶评判。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当今,尤其是中国法学院,法律和制度的学习和研究太容易失去社会历史语境,失去针对性,既不针对困扰人的一般性难题,也不考虑具体时空地理。原本针对具体时空中具体问题创造、衍生发展出来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成了答案,成了信条,然后就成了教条,只能遵循和恪守,最多略加演算和演绎,却不能生动鲜猛地刺激当下中国法律人创造性地思考和应对他们面对的复杂难题。但问题(question)会有答案,难题(problem)则没有,只能解决,创造性地解决,更多时候则只能应对,也就是“耗”,但这时问题就成了,怎么“耗”?对于现代以来的中国来说,如果失去了具体针对性,不关心具体时空中的那个难题,仅抽象讨论法律制度,或讨论抽象的法律和制度,自然就说不出什么道理。没有问题,又没有道理,就一定枯燥乏味,就一定说不出历史中国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遇上近代来自西方的说出了它们自身某些道理的理论之际,旁边还有令人眼晕的西方的经济繁荣,就很容易自惭形秽,“月亮是外国的圆”了。
宪制/法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领域。如今太多法律学者,即便不是宪法学者,都可以侃侃而谈,联邦制,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表达自由,同等保护,正当程序,甚至州际贸易。我也不反对,不认为错。问题是,仅此不够,太不够了。因为所有这些被抽象表达的制度法律实践都同特定时空语境相联系,其正当性、合理性、有效性以及局限性都受限于具体语境。在美国,其实,这些也都是在时间中慢慢展开的。想想,虽然美国宪法文件中早就写了,但“言论自由”是直到1914年才进入美国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这就是时空问题。想想,如果今人穿越到秦汉,能否用这些西洋制度法律原则有效应对匈奴袭扰或“七国之乱”?
我不是目的论者。意思是,我不认为,有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奔着什么去的,包括创立和建设这个中国。但话都说到这份上,也必须承认,如霍姆斯所言,就实践而言,人注定是地方性的。既然我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就想展示,也自觉有责任展示,有着沉重肉身而不是仅有灵魂或思想的一些人,我们的先人,在这片特定土地上,在这块后来才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活下去,为活得稍稍好一些,以什么样的智慧或“极精炼的愚蠢”(罗素语),一代代合作、演进和积累,造就了如此的中国。我力求展示,即便在一些人特别是某些今人看来的野蛮或愚蠢,也不是全然没有理由和根据的,或是不正当的。一个群体的长期“愚蠢”,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很可能就是他们在生存的具体情境中被逼出来的唯一选项,因别无选择,所以是智慧。制度是否智慧其实可以以种群的生存来判断。在大致同等条件下,再怎么矫情,你也不能说一个“败家子”智慧吧!即便你可以夸奖,比方说戈尔巴乔夫,有善良的情怀。也因此,真正实践性的制度智慧是很难解说的,甚或就不需要解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进这个行当就要40年了,我还是没法信仰法治或宪政!
但这些前人的智慧如今需要解说了。上小学时就知道,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科举和皇帝,诸如此类的。这些制度对于中国的宪制意义,对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政治文化精英来说,也许是一目了然,根本无需分析展示,无需理论逻辑来演绎。面对着紧要急迫的生存和治国难题,他们总是精炼地断言,诸如“齐家治国平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类的,不说理由,也不容分说。若你总不明白,那——也许你就不是这个“料”。他们不说道理,只是一代代用历史叙事,相互交流并传承。
也很有道理。这个世界从来也没法,没打算也没责任,让每个人都理解历史中国的制度,即便你也识几个字。理解的人也不会生活得更好或更幸福。但由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文化下移,教育普及,也由于当代长时段的和平,对于一直待在大学校园的起码这两三代法律人来说,以及对于以——甚或有时只能以——“萝卜多了不洗泥”方式出品的法学生来说,即便他们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追求,只要不置身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语境,也很难理解这些历史制度曾经和至今的伟大意义。真正的伟大会融入生活,成为常规,成为背景,因此不彰显,因此看不清其发生和存在的理由——再重复一次“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今天的学人很难首先察觉已融入日常生活的那些规矩和制度,更难经此想象性重构当初催生这些制度的、那些曾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难题。这些难题并没完全消失,至今仍以各种方式潜伏或隐匿在我们身边。但有时,恰恰由于这些制度颇为有效,乃至会令我们觉得似乎从来就没有这些难题,不会有,也不应当有;有的只是,只能是,当下西方宪法话语提出和讲述的那些问题。乃至,可能会有人感叹,秦始皇为何当初不试试联邦制呢?刘邦为什么只“约法三章”,为啥就约不出个《大宪章》呢!
夸张了?其实未必。民国时期不就有一批大名鼎鼎的学人埋怨中国当初为什么采取的是方块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废……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卷4,第4 期。但这不是钱玄同一人的主张,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均持这一主张。并要求,还不光是他自己,而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今天我们不抱怨方块字了,在“不如人”上,也不那么绝对了;但在法学和法律上,这种心态还挺重。周边这种嘴脸仍不时出现。
不论有多大的胸怀,真正的学术其实只可能是个人视角。个人视角就一定有偏颇。可以偏颇,但不等于不通情达理。我想用一种不按时间排列整理事件的方式,即围绕问题讲道理的方式来展示中国宪制及其实践,说说历史行动者曾面对的重大约束、难题和他们的制度选择。更一般地说,我想用中国历史的宪制经验,来揭示一般宪制可能或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现有的宪制或宪法律理论都过于单薄,尽管不明觉厉的高大上概念越来越多了;有时连修辞都缺乏,只剩下口号和语词了。非但回答不了几十年来如欧盟的问题,而且,在美国,总爱用正当程序或同等保护等条款,看似在回应,其实是在隐藏或遮蔽一些更关键的宪制问题。这种高调但无用的宪法理论肥大症正向中国法学界蔓延。
仅从法学角度解说历史中国的些许常识,就一定会有在其他学者看来不合理的取舍、误解和大量遗漏。但说到底,本书只是对中国历史或经验的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概括复述。这种复述力求讲出理由。因为,自中国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我们面对的世界变了,学术话语的受众变了。我们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有必要以社会科学的进路来讲讲中国宪制的道理;“五四”以来文化的全方位下移,令中国受众扩展了,也必须扩展,不再只是少数政治文化精英了。
即便努力,也不就能完成追求。这受制于我个人的狭隘视角,但更受制于我贫乏的知识和学术想象力。即便书稿完成了,我也会想,这是不是自我安慰?并因此是特定意义上的自我欺骗?!这类反省注定了我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诚惶诚恐。但任何人的视野、知识、理解力和想象力都注定有局限;我也就只能不为自己的智力低下或智识薄弱过度羞愧了。那会误正事。真值得羞愧的,在我看来,是为了学术的高大上或全面或政治正确而时刻关注“历史潮流”,终身追求“真理”,并从此加入了安全的滥竽充数。中国的学术时代正在到来,一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甚至外国学人,会,且能,重新阐发历史中国的那些有宪制意义的制度和实践。
本书也没打算一定要说服谁。不可能通过论辩让一个人喜欢上什么,比方说一杯啤酒——好像是霍姆斯说的;也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留给我的选项其实只是,如艾略特在《救生岩》(The Dry Salvages)中的告诫:“不是划得漂亮,而是向前划,水手们!”
得感谢这个时代,互联网大大方便了这一追求。许多资料甚至是少年时看的,很有感触,却没留心,就算知道个大概,也很难查找落实。查找的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会掐死查找的念想。互联网便利了查询,便利针对问题集中阅读,包括核对那些不标明出处和页码似乎不合适的文献。
但这种研究和写作方式也会引发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另一种注“水”,即堆积大量资料和引文,看似资料翔实,却缺乏集中的学术关注或问题,严谨的内在逻辑和强有力的理论论证表达。为避免“水”,一如既往,我先分专题写作,力求每一章甚或一个附录都能按论文的标准来写。事实上,本书大多数篇章都曾发表,这里就不一一致谢最先发表的各刊。但本书又绝非论文的简单汇集。本书主题集中,各章互补,论证分析自然相互牵扯勾连。非但总体一定大于简单的汇合;而且修改定稿中,我有大量调整、删减、修改、增补,许多段落几乎完全重写,有些篇章则是全新的,不曾发表。不全是为了对得起读者,其实更想对得起自己——毕竟人生苦短!
这至少部分解说了为什么本书拖沓了至少两年。就算对得起读者了,也一定对不起许多一直关心并以各种方式令我写作获益的朋友,也没法在此一一列名了。对一直以各种方式敦促我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白丽丽编辑,我更深感歉意。好在完成了,结果好,一切都好!谢谢各位朋友了!
苏力2017年8月31日于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明楼